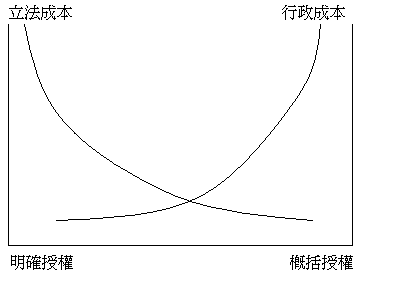 |
授權明確性原則之法理分析與經濟分析
最後修改:2002年10月20日
楊智傑*
摘要
本文主要是想要批判檢討從德國引進的授權明確性原則。該原則非我國憲法規定,但透過留德學者的大力引介,大法官也從善如流,自釋字第三一三號開始,大量使用,並且於法學者主導的行政程序法中,立為明文。筆者於本文主張兩點質疑:一、立法機關對於模糊的授權,本有自己的事後監督機制,但是這個機制似乎被公法學者與大法官們刻意忽視。當立法機關有權廢止逾越授權的行政命令而不願行使時,司法機關適合出來高呼它逾越授權嗎?二、當德國學者號稱授權明確性原則可以從法治國原則和民主原則當然推導出來,而不待憲法規定時,學界似乎也未注意到,一樣是強調法治與民主的美國,卻漸漸架空該國類似的原則:禁止授權原則。其背後有什麼不同的思考呢?
除了澄清立法機關自己的監督控制機制,與比較法的對照外,本文也試圖將此個案,納入到整個台灣法學研究進路的大環境中,點出以外國法為尊的自然法思想,而這樣的自然法思想,更是透過司法違憲審查的運作,輕易成為台灣的實在法。此外,本文更嘗試將法律製造類比為一般的產品生產,套用簡單的經濟學觀念,對是否應該明確授權進行經濟分析。最後總結一切論點,筆者認為,授權明確性原則不是個好原則。
我國大法官對於法規命令(授權命令)[1]的違憲審查,最常見用來宣告其違憲的理由,莫過於所謂的「授權明確性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意指立法院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制定法規命令時,其授權的「目的、內容、範圍」必須具體明確。此原則在大法官初次於釋字第三一三號正式引進台灣時,並非台灣的實定法,而乃源自於德國的基本法(該國憲法)第八十條第一項:「德國基本法第八十條第一項規定:「聯邦政府、聯邦各部部長或邦政府,得根據法律發布行政命令。此項授權之內容、目的及範圍,應以法律定之。…」我國憲法雖然沒有授權明確性原則的明文規定,但是學者認為這可以從憲法中的法治國原則與民主原則中自然推出,而無待規定[2]。因而,我國學者多引用此一德國原則,來要求立法院在授權行政機關制定法規命令時,必須符合此一明確性原則。
然而,台灣的授權條文,長久以來都是不明確的,最普遍的就是在母法的最後一條說:「本法施行細節由主管機關制定。」至於施行細則到底要寫什麼,根本沒說清楚,完全不符合授權明確性的要求。所以,在大法官自釋字三一三號引進這個原則後,幾乎所有台灣的法規命令都陷於違憲的邊緣[3],只差某個人提起憲法訴訟的臨門一腳罷了。大法官眼看不對勁,又在其後的解釋中,稍微緩和了「授權明確性原則」嚴格的要求,改口說,只要參酌該法法律整體所流露出來的立法精神,即可作為授權的標準。
如今,隨著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授權明確性原則也於該法第一百五十條第二項被明文化:「法規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
不過,有趣的是行政程序法的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本法施行前,行政機關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訂定之命令,須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者,應於本法…,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後修訂或訂定;逾期失效。」這個條文要求所有在行政程序法制定前,母法的授權條款不符合授權明確性,並因而制定出來的法規命令,必須在一定期間內全部修正完成,以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的要求,否則一旦逾期,兩者都將失效。不過,這個條文的歷史頗為坎坷,在一九九九年該法剛制定好公佈時,並沒有這個條文,到了二○○○年年底,行政程序法正式實施前夕,加訂了這一條,沒想到到了二○○一年的六月,它再度被修改,命運實在多桀。
這條被修改的理由很簡單,因為行政機關制定的法規命令實在太多,且多半未有明確授權。行政機關目前的因應方式,並非是將無授權依據的法規命令修改到符合當初授權的範圍,而是一一檢討其授權的母法,倘若其授權條款不夠具體明確,則自行擬定母法的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去。目前則因這樣的修正草案太多,全部都被擋在立法院內,通過的速度緩慢,所以到了第一次限定的時間到了後,還是沒辦法完成所有的修正工作,最後只好直接修正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讓立法機關喘口氣。
本文之目的,是想點出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這樣的紛紛擾擾,浪費諸多行政成本、立法成本,其實都是學者無端引進外國學理而引發的一場鬧劇,是不必要的。本文想藉由美國關於禁止授權原則的歷史發展,告訴大法官,授權明確性原則並非絕對,也不是如留德學者所謂是法治國原則的當然產物。甫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一方面把授權明確性原則明文化,一方面卻對行政命令的制定程序引進美國的行政程序法的規定,但是,美國因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某程度卻放寬授權明確性要求,為何我們反而決定兼採兩國之美,兼容並蓄,令人納悶。
其實要檢討授權明確性原則,第一個需要批判的,就是名不符實,亦即所謂要求授權時對所授的目的、內容、範圍要具體明確的要求,是針對立法機關,而與行政機關逾越授權時該如何如何,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但是學界似乎是積非成是,都以「授權明確性原則」來對付逾越授權時的情形。例如,以最簡單的釋字三九○號為例,大法官先開宗明義地幫我們複習了一次授權明確性原則的要求,但是後來的結論卻是,由於系爭行政命令欠缺法律授權之依據,因而違憲。「授權明確與否」與「是否逾越授權」這兩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聯,面對一個授權很明確的母法,行政機關還是有很能制定出逾越授權的子法出來,但是學界與大法官卻習慣將兩者混為一談。
追究為何以概念清晰、邏輯嚴謹自我標榜的法學界,會犯下這個錯誤,並且早有人察覺指出[4],卻始終不願更改的原因,最可能的答案,莫過於是「一味繼授」的心態使然。
簡單回顧一下我國授權明確性原則的發展。前言說過,授權明確性原則乃是德國基本法第八十條的內容,並非我過的憲法規定,一九九○年,留德學者許宗力教授於《台大法學論叢》十九卷二期發表了<行政命令授權明確性原則之研究>,首度完整介紹並倡議引入該原則,他說,雖然我國沒有類似德國基本法第八十條的規定,但是授權明確性原則卻是法治國原則或民主原則的當然產物,就算憲法沒有規定,我國也該力行遵守[5]。後來,在一九九三年,大法官受到了學界的影響,首度在釋字第三一三號的解釋文中,正式引進了德國的授權明確性原則,而後開始廣泛使用。不過,大法官雖然每次都告訴我們法律授權時應該就授權的目的、內容、範圍要具體明確,卻從來沒有一次說到,究竟違反的效果為何,而每次宣告違憲的理由,只是因為行政命令逾越授權範圍。
我們可以從引進這個原則的過程很清楚地發現,我們從來都沒有正確地引進授權明確性原則。
德國的授權明確性原則的規範對象是立法機關,違憲審查的客體是法律[6],美國的禁止授權原則亦然[7],可是,我們針對的對象卻是行政機關,違憲審查的對象卻是行政命令,而且與授權明不明確全然無關。
從以上兩點:一、明明憲法沒有規定卻硬說是法治國原則與民主原則的當然產物,二、明明內容不同還硬要套德國的名稱,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國內的大法官、學者是如何地一廂情願,憲法的內容,是多麼地容易受到主事者的主觀偏好影響(請參考陸、自然法思想與違憲審查)。
授權明確性原則在我國大法官會議的具體運用上,其實是用來指責行政機關所制定出來的行政命令,逾越了母法的授權,其常用的用語為「逾越授權範圍」、「逾越法律授權」、「增加母法所無之限制」、「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等[8]。看起來,大法官所不同意者,是行政命令逾越了「母法」的授權,但是本質上,其乃是逾越了「立法機關」的授權。或許,有人會認為,「母法」和「立法機關」是不同的,不可混為一談,但是,如果想到對行政命令及母法本身的終極主宰者,還是立法機關時,就知道如果一個行政命令逾越了母法的授權,但是卻不逾越立法機關的想法,硬是要讓它違憲,既無意義,又浪費成本。
此段筆者想要提醒讀者另一個我國學者與大法官刻意忽略的制度,若同時思考到這個制度的存在,就會發現大法官單純因為行政命令逾越法律授權就宣告其違憲的不適當。那個制度就是:立法機關在對行政機關授權後的事後控制機制。
立法者並不笨,他們在授權給行政機關制定行政命令時,除了可能自發性地啟動事前的監督機制--亦即對行政命令的目的、內容、範圍明確限定--外,也設計了一套事後的監督機制,以對付那些不符合立法者口味的行政命令。這種事後的控制機制,主要就是規定行政機關在依授權制定好行政命令後,要送回給立法機關,讓立法院再檢查一次,如果立法機關覺得可以,那就沒有問題,反之,如果立法機關認為不可以,那麼就會對該行政命令施加一些對策。
德國國會對於授權立法的監督,主要有四種模式,一是同意權之保留,二是廢棄請求權之保留,三是國會聽證權之保留,四是課予單純送置義務[9]。而美國國會對於授權立法的監督,也有多種的事後監督機制,包括被聯邦最高法院宣告違憲的「立法否決權」[10]。
我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規定,行政機關制定行政命令後,應即送立法院。至於送到立法院後,立法院能如何處理,在以前立法院議事規則第八條有規定,立法院認為該行政命令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可以經過決議,通知原機關更正或廢止之。有學者認為該議事規則既非法律,且所謂「決議」並非正式的三讀程序,所以對於行政機關不具拘束力,頂多屬於德國法制下的單純課予送置義務而已[11]。不過這樣的講法是否合理,也引起了學者的批評,認為立法權本來就屬立法院所有,立法院用議事規則來規定對行政命令的監督,算是國會自治的範圍,對行政機關當然具有拘束力[12]。
不過現在關於立法院監督行政命令,規定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所以前述批評議事規則並非法律的質疑已經不成立,且在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所謂議決,準用法律案的議決,所以應該也符合立法的三讀程序。故現在立法院基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而要求行政機關廢止或更政行政命令,應具有法律的拘束力,觀其內容,應屬於德國所謂的廢棄請求權之保留。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所有的職權命令與授權命令,訂定後都要送到立法院,倘若立法院對於該行政命令認為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而以命令定之者, 如有三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即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第六十條)。委員會應於三個月內完成審查,逾期未完成者,視為已經審查,但得要求延展一次(第六十一條)。若發現被審查的行政命令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而以命令定之者,應提報院會,經議決後,通知原定頒機關更正或廢止之;該機關應於二個月內更正或廢止之,逾期未更正或廢止者,該命令失效(第六十二條)。
介紹了這個由我國立法院自行發展出來、早就行之有年的事後監督機制,相信讀者一定不難發現一個簡單的問題,亦即:如果一個行政機關所制定出來的行政命令,雖然可能沒有明確的授權依據,但是送到立法院後,立法院發覺行政機關的版本不錯,因而決定不行使自己的權力:將其廢止或要求更正之,那麼,在經過這一套過程後,這個行政命令雖然逾越了當初母法的授權,但卻是當前的立法者所同意的行政命令,這樣,司法機關有必要再去宣告其違憲嗎?
之所以立法機關會選擇廣泛和模糊的授權,有可能是因為自己無能力提供明確的授權標準,不如廣泛授權,反正自己事後還有一個監督機制(美國國會正是出於此心態設計出事後監督機制[13]),換句話說,立法機關對於授權立法,明明自己就有權力加以監督控制,不用司法機關幫忙,而在立法機關對該法規命令逾越原始的授權沒有意見、不願行使自己的權力時,司法機關根本不必要去質疑該法規命令逾越授權。這一整套立法機關自己設計出來的監督機制,留德學者和大法官卻只看到前半段,就跳進來說法規命令違憲。
在德國,對於國會能否以事後監督的機制(尤其是保留同意權),產生了很大的爭議。至今為止,聯邦憲法法院的立場頂多採取了折衷說,原則上認為不可以,但例外認為可以,並沒有全面地認同國會的事後監督[14]。採否定說很強的理由是認為,既然國會事前已經有很明確的授權了,事後就不應該再介入,保持權力分立。也就是說,他們頂多認可一層監督機制[15]。我國憲法既未明文規定授權明確性的要求,立法者又自己選擇了事後監督機制(當然立法者也可以事前明確授權),為何在學者鼓吹下,大法官就自己不明究理地跳出來,然後要求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照辦,此不但漠視我國立法實務上的運作(大部分的法規命令授權都不明確),而且還用自己發明的東西到處宣告法規命令違憲?﹗
留德學者除了說授權明確性原則可以從民主原則中推導出來,無待憲法規定[16]。其實,若考量進立法機關的事後承認的監督機制後,根本不能說哪裡違反民主原則。實際上,立法委員可以透過事後監督的機制,來貫徹其職務,該行政命令也不至於逸脫立法委員的控制;而在政治責任方面,關心的選民一樣可以檢驗立法委員的授權過程與結果。
英國分析實證主義法學者奧斯丁說過:「由於國家可以廢棄他(法官)所造的規則,但卻允許他根據政治社會的權力去執行這些規則,所以儘管國家不是通過明確的聲明,但它的行為明確地表明了『他所造的規則將會獲得如法律一般的』最高意志。」[17]奧斯丁這段解釋法院的判決因為有國會的默示同意而有拘束力的理由,一樣可以用在行政機關的行政命令身上。
立法機關若對法院的判決有所不滿,是透過立法的方式推翻其判決,而不會說法院逾越了立法的本意諸如此類的話,同樣地,若立法機關對行政命令有所不滿,它自己有辦法更改這個行政命令,它既然不更改,法院這時候跳出來說這個行政命令逾越了法律的授權,似乎沒什麼道理。或許可以比擬作民法上的代理問題來思考:無權代理時是效力未定,如果本人予已承認,就對本人有效[18]。既然國會已經以不推翻行政機關送來的行政命令,默示承認了該逾越授權的部分,這樣的動作就代表了其不違背本人(立法機關)的意思。
立法程序的立法模式有許多種,有些國家要求法案只能由國會議員提出(例如美國),有些國家則沒有這個限制(例如我國),那麼,難道就不能有一種是讓行政機關先去制定行政命令,然後國會再予以糾正的立法模式嗎?同樣是某個行政機關制定的一套規定,一種是當成法律草案送到立法院、由立法院「明示地」以立法方式通過,另一種則是先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通過,立法院再以要求送審的程序加以「默示地」承認,這兩種應該沒有那麼大的不同。既然立法院透過事後監督的機制,已經算是同意了該法規命令,為該法規命令背書,其實可以等同是立法者自己的立法,司法機關若想審查,為實質審查就好,不必要在程序上作文章。
而且從立法實務上來看,現在的立法程序,多半都是行政機關寫好草案,才送立法院審議,其實多數的立法形成,在行政機關那裡就已經決定了大部分,而立法院就僅掌握了最後一道的防護網,以確保這些草案沒問題,這與行政命令的事後監督有何不同?或有認為行政命令的事後監督,立法院不一定都送委員會審查,只有在三十位立法委員連署或附議時,才會用到三讀程序,但這還是已經給了立法機關一個控制的機會,況且每年年終立法院法案大清倉,立法委員也未必就真的有把法律看過了。不論是行政命令或是送審的法律草案,它們兩者的相同點,就是立法機關最後都有一個機會說不。
從功能的觀點來看,這兩者並無太大的差異,實務上雖然立法院對送審的行政命令很少審查,但這也是因為立法者在母法中把重要問題都處理了,可以對授權所訂定的法規命令不用太操心。這裡或許可以用美國在討論三權分立時所爭辯的形式論與功能論的區別來討論[19]。功能論者認為,只要制度的設計不危及各權力的核心功能或權力以及權力之間的制衡關係,就可以允許[20]。立法者不選擇事前明確授權,而選擇了事後的監督機制,實際上已經達到了立法的功能,司法者根本沒有必要越俎代庖運用授權明確性來宣告法規命令為憲。
至於有謂立法委員會利用授權、逃脫政治責任、讓選民無法監督、以致違背民主原則一說,實際上會關心立法委員特定選擇的人,也一樣可以關心立法委員選擇授權的行為,更可以關心立法委員事後監督的態度[21];相對地,不關心立法委員特定選擇的人(通常只關心其意識形態),則三者都不關心[22]。另外,也有學者指出,就算用授權明確性原則試圖讓立法委員在特定議題上表態,好讓選民有所憑據對之課與政治責任,實際上立法委員仍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脫逃而不表態[23]。
德國所謂的法治國原則,用英文來說,就是rule of law,也可稱為法治原則。法治國原則或者法治原則是一個相當空泛的概念,空泛到幾乎是每個學者偏好什麼內容,就可以說它是法治國原則下的內涵、是其子原則。例如,美國有名的自然法學者富勒,其所謂的程序自然法(或法律的內在道德),也稱作「法制原則」,其實也就是指法治國原則[24]。他自己盧列了八項法制原則應有的內涵,認為不符合這八項內涵的法規就不具有正當性。富勒之所以被歸類為自然法學者,就是因為他所主張的法治原則,並非實在法的要求,而是他自己認為該要有的,而這正是我們對自然法的定義。
同樣地,德國學者也是如此的自然法,對於法治國原則這一大框框,其更是無所顧忌地填入自己所希望的諸種想法。德國學界最近也開始出現反省,認為法治國原則被使用得過度氾濫,而開始討論這個原則的核心內涵,以限縮學者無限制的擴大[25]。
德國學者既然都已開始反省,我國應該也沒有必要說授權明確性原則是法治國原則的當然產物。
以下將會介紹,同樣是強調法治原則的美國,原本也有類似授權明確性原則的「禁止授權原則」,卻在法院判決演變中,因為受到實用哲學的影響,漸漸架空了該原則,而今幾乎允許極為廣泛和模糊的授權。當留德學者告訴我們,授權明確性原則是法治國原則的當然產物,且大法官也欣然接受後,本文這一部分是想以美國禁止授權原則的發展以作為對照。
美國憲法第一條說:「所有的立法權力應該授權給聯邦議會。」這個條款一方面授權國會,一方面也是使用立法權上的限制。它禁止國會將它的立法權再度授權給其他機構。這個限制,稱為「禁止授權原則」(nondelegation doctrine)[26],是用在檢驗國會授權給行政機關時是否「廣泛」(broad)或是「模糊」(vague),而有可能違憲的情形。
以下開始介紹美國關於禁止授權原則發展的歷史[27]。
禁止授權員則於美國的發展約略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期是「新政時期之前」[28]。一八一三年,最高法院在Brig Aurora案中,第一次處理禁止授權原則的問題,而提出了所謂「講明的情況」(named contingency)標準[29]。不過,後來一碰到無法通過這個標準的案子,這個標準就被廢棄不用了。在Buttfield v. Stranahan案中,法院改採「標準提供」(standard)檢驗標準,所謂的標準提供檢驗標準,就是看國會有無提供足夠的的標準以清楚的限定授權的範圍[30]。不過,如果無法順利通過標準提供標準,法院也會考量立法的歷史。簡言之,法院不傾向依循嚴格的禁止授權原則,反而是實際地要求國會提供「可理解原則」(intelligible principle)[31],讓行政機關遵守以及得以讓司法者有標準審查行政機關是否遵守國會的意志。不但如此,法院也會用立法和行政的歷史來找出明確的定義以調和模糊的授權。
第二個時期是「新政時期」[32]。法院中止了之前傾向於接受廣泛和模糊的授權,開始回復禁止授權原則。在Panama Refining Co. v. Ryan案[33]中,法院認為國會對總統的授權,無法通過「標準提供」(standerd)檢驗標準。後來在A.L.A. Schechter Poultry Corp. v. United States案[34],法院則認為其授權範圍太過廣泛,且在實現其授權時,未採「對辯程序」(adversary procedures),包括了聽證和司法審查,故將該法宣告違憲。由於在新政時期過後法院又開始回復接受廣泛和模糊的授權,所以多數人認為新政時期案子是反常的,而且是基於法官們反羅斯福政府的意識形態所致。事實上,這兩個案子是整個禁止授權原則發展歷史中,唯二的兩個被最高法院宣告違憲的案子[35]。不過,法院在這時期的分析對往後的案子仍很重要。法院並非推翻之前的判決,而是宣示授權標準明確的程度必須與所授權力的範圍程度相關,也與對人民的程序保障相關。
第三個時期是「後新政時期」[36]。自從新政時期過後,最高法院在審理與禁止授權原則相關的案子中,幾乎接受所有的立法授權。有些案子,法院採用卡多佐法官在Panama Refining Co. v. Ryan案的方法,認為法律前言中所述的立法目的可視為授權的必要標準。有些案子,法院則採用Buttfield v. Stranahan案的方法,利用立法的歷史與行政慣例以對模糊的字句提供較狹窄的定義。如此,法院寧願在解讀法條時選擇一、或二、或多的狹義定義,讓行政機關至少擁有一些權力,以避免掉違反禁止授權原則的問題。法院通常會透過各種解釋方法來說明授權是明確的。例如,法院認為,在戰爭及外交領域,行政部門需要更多的彈性,所以給予國會授權時較大的裁量空間。法院甚至部分基於下列理由來正當化其模糊的授權:如果行政機關違背國會的意志,國會可以透過事後監督或是直接立法來更正[37]。此外,在Amalgamated Meat Workers v. Connally此一聯邦上訴法院的案件中,法官認為其不違反禁制授權原則的理由之一,即包括:其有適用行政程序法,故符合Schechter案所要求的程序保障(包括司法審查)[38]。
第四個時期,則是「試圖復甦禁止授權原則卻挫敗的時期」[39]。在這個時期中,聯邦最高法院的院長Rehnquist法官,在Industrial Union Department v.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案[40]和American Textile Manufacturers Instiyuye, Inc. v. Donovan案[41]中,試圖復甦禁制止授權原則,但卻沒有贏得多數法官的支持。在Mistretta v. United States案[42]中,最高法院再度強烈的表達了他們的立場:不願意復甦禁止授權原則以作為對行政裁量的審查。該案是國會授權給聯邦刑事委員會,對聯邦法院制定發布有拘束力的刑事判斷指引。有人因此挑戰其合憲性,不過被法院駁回了。法院認為這個案子中的授權指示,比之前其他已通過禁止授權原則檢驗的法律還要明確多了,而且照慣例法院也認為國會已提供了可理解的原則[43]。
在美國法院接受廣泛和模糊的授權歷史中,除了實用哲學影響外,還參雜著經濟分析的理由。另外,還有一個有趣的理由,對我們台灣的行政程序法是種諷刺。那就是法院認為,如果已經有提供嚴格的程序要求,那麼是否逾越授權也就不那麼重要了,也就是筆者所謂的「功能互補」。美國法院說到,由於有符合行政程序法的嚴格程序要求,所以授權不明確也沒關係。這個「功能互補」的方式,已有學者提出建議,其稱之為「多元工具下的最適工具」[44],另外,湯德宗教授於行政程序法未通過前,曾特別提到美國的這種「授權」和「程序」的「抵換」(trade-off)關係,亦即提議既然制定了這麼繁瑣的程序,或許就可以不用那麼強調授權的要求[45]。但最後沒被採用。
所謂的程序要求,可能是行政命令的制定程序,或者是依據行政命令作成行政處分時的程序。由於美國的行政命令正式制定程序要求事先公告、舉行聽證、並且得依聽證紀錄來制定行政命令,強調民主參與,所以在盡了這一長串的程序要求後,再來說什麼授權不明確、逾越授權,實在不太妥當,所以法院也基於這個理由,認為廣泛模糊授權沒關係。
我們這次的行政程序法對於法規命令的制定程序,一方面引進了美國的聽證制度,另一方面也將德國的授權明確性原則明文化。而在行政處分的作成,也同樣採用美式的嚴格程序。諷刺的是,我們擺脫不了的繼受性格,一方面全部引進美國對於行政命令的制定程序,卻沒有發現美國的實務運作如何(某程序因為有此嚴格程序要求而放寬對授權的限制),反而兼容並蓄,德國的也採,美國的也要,使台灣成為一個最沒競爭力的國家。
前言提到過行政程序法制定以來,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紛紛擾擾的修訂過程。目前,各行政機關對行政程序法的因應是,一一檢查其下的子法,看看是否有明確的授權依據,倘若無,則趕緊提出一個母法的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待立法院通過。筆者搜尋近一年報紙有關行政程序法相關新聞,其內容都是同一個模式,那就是先報導某個行政命令將因為行政程序法而面臨失效,但是接著主管官員都提到,目前已經對授權母法擬訂修正草案,待通後則法源依據就沒有問題。這類的報導為數不少,例如:2001/9/3工商時報<境外航運中心缺少法源依據 解套有腹案>、2001/10/21聯合報九版<內政部廢止遭飛彈襲擊處理辦法 國內生化防護 陷入空窗期>等。事實上,立法院大多會通過這樣的授權修正案[46],畢竟從增訂授權條文的條文中,立法機關也看不太出來究竟修正了什麼。從這樣的行動我們可以發現,我們國家的行政命令並沒有因為授權明確性的要求而更保障人民權益,因為實質的內容都沒變。反之,我們只看到了一件事,那就是這樣的要求耗費大量行政成本,拖垮立法程序[47]。雖然這次再度修正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讓立法院鬆了一口氣,但是基本的問題卻沒有解決,那就是許多這樣沒有實質意義的立法,會排擠到其他具實質意義的立法(例如加入WTO的相關配套法案),浪費立法資源。
以下筆者簡單整理一些美國學界對授權立法進行經濟分析的一些討論,並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簡單的經濟分析,說明要求授權明確的不智,以及解釋為何會出現台灣目前的困境。
根據Peter Aranson、Ernest Gellhorn、Glen Robinson三人於<A theory of Legislative Delegation>一文中指出,立法委員主要是在兩種情況下會選擇廣泛授權。第一種情形是,立法委員發現,這個法案會對其選區中的某些選民有好處,同時也對選區中的其他選民有壞處,他為了在下次選舉中取信於前者並避免失信於後者,他寧可選擇廣泛授權,由行政機關去做實質決定,而不要髒了自己的手。第二種情況是,選區中的選民對這個法案的意見相左,不過他們都願意通過新法,只是對新法的某些內容無法協調出一個大家都滿意的方案,立法委員為了怕得罪任何一方,寧可選擇模糊的授權,如此一來新法既然通過了,選民都很開心,不過對於實質問題上的小爭議,就交由行政機關去解決,怪也怪不到立法委員的頭上[49]。而且對立法委員來說,這樣的好處是,一方面他可以說他為這樣的法案貢獻了心力,一方面當行政機關做出了實質決定後他可以替人民抱不平[50]。
根據上面的分析,作者們發現,透過廣泛授權的方式,立法機關容易通過較多的法案。而基於某些公共選擇學者的看法:立法委員們通過立法,都是站在為自己與自己選區選民的好處,而去犧牲公共福利[51]。所以他們主張,不應該廣泛授權,如此才能減少立法的數量,也因而能減少為了特定族群犧牲公共福利的機會[52]。
不過,這個觀點充滿矛盾。本身的立論上,如果真的認為立法委員的立法,都是利用公共資源遂行私人目的的話,那麼根本就是反對整個立法院這個組織,又怎麼希望立法委員不要廣泛授權,而應該將大部分的實質決策權留給自己行使呢?而且,如果認為立法委員間的利益交換(logrolling,投票交易)情形嚴重,那麼將政策決定廣泛授權給行政機關,不是更能讓其決定免於受到利益團體的影響嗎[53]?雖然該文提到行政關也會有自己的誘因去分配資源[54],但其解釋過為遷強,不具說服力,實際上行政機關比起立法機關,較不會有被特殊利益團體把持的現象。
立法機關的立法,究竟是會造成社會整體更多的損失,還是增加更多的福祉?這其實是公共選擇學派最重要的爭議所在。原則上,如果一個法律真的是利用公共資源於少數利益團體上,那麼該法律的社會成本高於其社會福利的機會很大。不過,事實上並非所有立法機關所通過的法律都是這種法律,這種法律的比例上在整體法律數量上所占不多,所以整體而言,通過越多的法律,相較於更多不合理分配資源的法律,其實也會有更多合理分配資源的法律,所以更多的法律,社會整體福利應該會增加才對。
越多的法律,尤其那些法律都是在有人需求的時候,會提高更多的社會福祉,這對一般人來說,是很直覺的事情,例如一般人多會希望立法院多通過一些早就擬定好的法案或修正條文,而不要都堆積在立法院的倉庫內,所以常會有人希望立法委員不要不務正業。一般說來,在對法律的製造做經濟分析時,我們多半假定通過法律對社會的福利為正值,而把焦點放在製造法律的與執行法律的成本上[55]。亦即,有同樣效用的法律,誰能用較低的成本來加以製造,則對社會整體而言是有利的。所以,下文將要討論法律製造成本的比較。
我們若將法律的生產過程拿來與一般的工廠製造產品的過程作類比,則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答案。
首先,我們先看看下面這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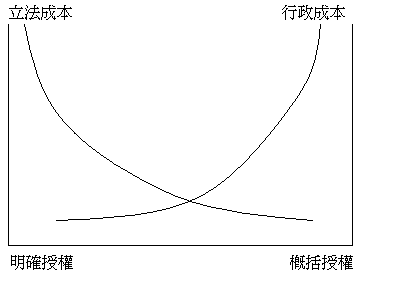
(取自Maxwell L. Stearns,Public Choice and Public Law: Reading and Commentary, Anderson Publishing Co. (1997), at 200)
這個圖是想要說明,如果要求立法機關明確授權,那麼法律的立法成本就會很高,但是若允許概括授權,則立法成本可以降低,但是卻會提高行政機關的行政成本(制定行政命令的成本)。所以,若能尋求出兩條線的交接點,則可以用最低的總成本,制定出法律和命令等規範。
然而,筆者認為,上面這個圖所能表達的概念,不夠貼近事實。一方面,這個圖沒辦法顯示立法機關的產能限制與邊際成本遞升的情形,而行政機關卻不太可能出現這些狀況。另外,以單一法律的立法成本與行政成本比較來看,行政機關由於專業的背景,其製造成本也會遠低於立法成本。
不但單一法律的行政製造成本,可能會遠低於單一法律的立法製造成本,總體而言,附予行政機關越多的任務,有時可能不會增加其成本,因為行政機關的人員任用是固定的,行政機關內本來就有專門負責草擬相關法律的人員,就算不授權給行政機關,他們一樣要替立法委員草擬草案,所以把工作授權給行政機關,可能其成本不會有顯著的增加。
每個工廠都有其產能的限制,立法機關也是[56]。面對現代行政國家大量的行政事務,立法機關若要對每一件事都進行明確的立法,或是在授權時提供明確的指示,則必定會增加立法機關許多負荷,導致其生產線擁塞,反而會讓許多更重要的法案,因為法案塞車而無法通過。例如,一個立法機關一個月最多能通過一百個法案,每一個法案有五十個條文,共五千條文。可是,如果每一個法案的授權都要提供明確指示,那麼原本只要一條概括授權的條文,變成為十個授權條文,則一百個法案總共會有六千個條文,但是立法機關一個月就是只能通過五千個條文,必然有一千個條文必須留到下個月才能審理。目前行政程序法要求補列授權依據的規定,導致許多無實質意義的立法堆滿了立法院,排擠掉其他更重要的法案,這正是立法院產能的限制使然。
相對於立法機關,行政機關當然也有產能限制,但是就每一個專業的主管機關來說,自己所需要制定的行政命令並非包山包海,而乃是侷限於其主管範圍,所以不太可能會瀕臨邊界產能。相對地,立法機關不像行政機關,可以將不同領域的行政命令交給不同的主管機關去制定,立法機關只有一個,審查法案的時候雖然可以由各委員會在進行分工,但是在通過法律的時後,還是只有一個機關,產量必然有上限[57]。
另外,附帶於產能限制的,其實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的邊際成本遞升的情形。亦即,若已經逼近產能限制邊緣,單一法律製成的邊際成本可能就會開始從遞降轉而開始遞升,而且是急速的上升[58]。
台灣目前經濟靠代工(OEM),想必每個人都對代工的流程多少有點認識。之所以想要代工,是基於專業分工的考量,將自己的產品,委託其他具有專業技術、規模經濟的廠商代為生產,降低自己的生產成本,並因而可以將自己的產業擴大[59]。
若把立法機關授權行政機關制定行政命令比喻成代工,對此問題就可以有進一步的認識。一般人比較不較不會有疑問的,是行政機關的確比立法機關專業,其制定行政命令的成本絕對比立法機關來的低。但是一般人比較有疑問的是其民主正當性的問題。不過,在考量到本文所提到的事後監督機制後,民主正當性的問題就不在存在。實際上的代工也會有監督[60],不可能完全放手讓代工廠商做。通常委託廠商要找代工廠商時,可能有幾種方式:一、委託廠商或許是自己提供設計圖,二、自己沒有能力提供設計圖,要求代工廠商拿出做好的樣品供挑選,或是三、委託廠商請代工廠商代為開發或設計,委託廠商再在事後挑選。上述三種情況中,第一種類似於立法機關在授權時提供明確指示,後兩種就很類似於立法機關先模糊授權,然後再在事後監督的模式。其實不管哪種模式,委託廠商都會有執行和監督機制,畢竟最後的產品是掛上自己的品牌出售,而非掛上代工廠商的。倘若代工廠商作出來的產品不合委託廠商的意,委託廠商也會要求代工廠商修改。
當然,監督代工也會付出成本,但是相較於自己立法,其成本便宜的多,但是成品的品質卻不會有所減損。立法代工過程可以區分為幾個成本,一個是立法機關自己立法的成本,一個是行政機關代工的成本,一個是立法機關監督的成本。只要立法機關自己立法的成本,大於後兩者的總合,那麼代工就是有效率的。實際上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觀念,例如我們常說批評人家的作品很容易,但是要自己創作卻很難。立法機關自己不具有專業能力立法,硬要自己立法會付出許多成本,拖延立法程序,但是若先概括授權,然後等行政機關制定好行政命令後再來批評,立法機關仍然可以批評地很嚴厲,達到民主負責的效果,但成本卻大大降低,能夠符合現代行政國家大量立法的需求。
不過,以目前行政程序法對行政命令制定程序的嚴格要求來說,筆者也不敢保證行政機關代工的成本,會比立法機關自己立法的成本低。但是,縱使行政機關代為制定行政命令的成本高於立法機關自己立法的成本,筆者還是認為,有必要採用代工模式。主要原因有二:一,行政機關比立法機關專業。二,立法機關的產能限制,使其無法應付現代行政國家大量的立法需求,必定得要將立法製造轉包給行政機關。畢竟,拖延法案的通過,對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折損更大,會造成更大的社會總體損失。
從留德學者大力提倡、大法官順水推舟而引進授權明確性原則的這個例子中,或許可以讓人觀察到司法違憲審查與我國法學研究進路的一點隱憂,本段簡略地將筆者的想法略述如下[61]。
從引進授權明確性原則的過程來看,很清楚地,在憲法的外衣下,潛藏著一股莫名的自然法潮流。雖然,憲政主義或憲法,本身就是十七世紀古典自然法思潮的產物,但是既然將之立為法,其就是想要在眾多的自然法思想中挑選其一,而不要再讓各個法學者各說各話,也讓權利能夠有明文依據。比起第一個制憲國家美國憲法中的人權法案,它的權利寫的較為具體,至少還有點指示作用,對照起我們的憲法中的基本人權,只是把每一種權利的名字寫下來,沒有任何具體的指引,這樣的條文真能告訴大法官,什麼該保護而什麼不該嗎?
一如我們常說一個什麼都會的人表示其沒有任何一樣專精,憲法中的基本人權也發生了同樣的情形。當憲法第七條到第十八條例舉了哪種基本人權該受保障後,在第二十二條又多一個概括條文,這似乎讓才剛說過的特別保障的人權,顯的不那麼特別了。而且當第二十三條又寫出了與之相對的四種利益時,憲法的基本人權令人懷疑真有那麼大的作用。
以和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類似的程序法的例子來說明這個矛盾。民事訴訟法新增定條文中的當事人訊問和證據調查等制度,其說為了保障當事人的財產權與國家的訴訟資源,所以要犧牲當事人自己的隱私權,簡單的說,學者用憲法的第十六條訴訟權、第二十二條財產權、隱私權、和第二十三條的國家利益,彼此權衡之下,發現隱私可以被犧牲。相對地,刑事訴訟法中的被告緘默權,卻總是隱私權勝出。舉這個例子的用意,只是想透過這個對比突顯出,憲法說了那麼多權利根本沒用,只要一個法律是A權利和B權利之間的衝突,或是A權利和國家的C利益發生衝突,光是列舉了基本人權,是完全沒用的。
二十三條中的「必要」,告訴了我們什麼?沒有,什麼都沒有。但是留學德國的學者和大法官告訴我們,有,它說了比例原則[62]。看起來這又是自然法滲入憲法中的一例。老實說,若真用比例原則,是不可能將那些要人民繫安全帶、戴安全帽的法律解釋為合憲的,但是若用功效主義(或法律經濟分析)的「最小的妨害成本」這一觀點就能解釋。又例如,禁止賭博和嫖妓,也都是不可能經過比例原則的檢驗的。「必要」兩個字真的是指比例原則嗎?還是這些例子只能告訴我們,所謂「必要」兩字即指比例原則的說法,那不過是留德的學者的自然法思想罷了。
需解釋一下這裡所用的自然法的意思。其實,大法官們的價值中心,可能不是以某位思想家為宗的自然法思想,簡單的說,應該是「德國主流憲法思想是怎麼樣,台灣的憲法也就應該是這個解釋」。若要為這種法學思想定個名字,或許可用「德國法制優越學派」予以概括之[63]。但之所以稱之為自然法思想,是因為本來自然法就只是一種態度,它沒有特定的內容,例如霍布斯和洛克的想法可以差之萬里,但都被歸為古典自然法思想。而留德學者努力將德國的制度、德國的學說、德國的憲法解釋,說成是台灣憲法的要求,大法官們也欣然接受,實際上卻根本無法從台灣憲法中推出來,這不正就是我們所描述的自然法的定義嗎﹗
「德國法制優越學派」或許可以擴充為「德、美法制優越學派」。從歷屆大法官的解釋中,發現大法官們身受其留學國背景所困,早期解釋文中是夾雜日文、德文與該國制度說明,現在則多了英文和美國的制度[64]。據法學史學者王泰升的觀察,之所以大法官解釋文中開始滲入英美法思潮,並不是有留美的學者當起大法官來,只是反映出,國內留美的學者多了,寫的文章多了,而大法官們「早上吃的早餐」正是那些文章,「和他們一起吃早餐的」正是那些留美學者[65]。而根據蘇永欽的觀察,大法官解釋大多只是順應社會變遷順水推舟,而只有在一些與人民感受不深的法治國原則的建立上,與社會變遷無關[66]。授權明確性原則正是包含在其所建立的法治國原則內,但這卻是德國定義下的法治國原則。
再回到程序法的例子。另一個大法官胡亂引進、早已引起學界爭論不休的重要憲法原則,就是所謂的「正當法律程序」。正當法律程序的內涵,其實類同於德國的比例原則[67],也是要對三個彼此對立的利益做衡量:對所侵害的私人利益影響多嚴重?所主張的程序保障多有效?以及這些程序保障限制了多少政府的利益[68]?在初次引進時,孫森焱與林永謀大法官就認為根本無須引入這個原則,因為其內涵可被德國的比例原則所涵蓋。而最終大法官也心虛地將「正當程序」與「比例原則」並用[69],證明了正當程序只是一個空的標籤,其內涵與比例原則並無差異。但是大法官為何要引進呢?或許,大法官心想,那是美國的學說,留美學者也提倡,畢竟一部中華民國憲法,總不能全是德國的名詞吧﹗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偏好,大法官也有,亦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自然法思想,認為怎樣的法律才是好的、才是不違憲的。可是,司法違憲審查這個制度,卻只讓大法官去決定自然法是什麼。而那樣的自然法,是大法官自己的自然法,不是人民的[70]。
筆者於本段想強調:一、從我國遷強地引入授權明確性原則這個例子,顯示出大法官與法學者們的自然法思想(主觀偏好)是如此的德國美國。二、也唯有司法違憲審查機制,能夠如此輕易地讓少數個人的自然法思想成為實在法。本文所討論的授權明確性原則,足堪證明:大法官的確可以將其主觀偏好帶到憲法解釋中,而且台灣多的是好例子。
授權明確性原則的使用,在我國發生了許多有趣的例子。例如,釋字四二三和五一一號,處理的都是行政命令中的以到案時間為罰鍰裁量標準的問題,結果一個合憲一個違憲。合憲的是釋字五一一號,大法官認為,雖然系爭行政命令沒有明確授權依據,但卻可以從法律整體精神中發現是允許該授權的,而釋字四二三號則是綜觀法律整體精神,實在沒辦法找到授權依據,所以違憲。問題是,如果這個制度本身是可以通過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的實質審查,那麼行政機關若認為執法上真有需要,還是可以提出母法修正草案,增加明確的授權依據,然後想必立法機關也沒有需要去杯葛,最後的結果是:這個制度仍然存在,只是一度被宣告違憲過,浪費過不少司法成本、行政成本、立法成本罷了。
更明顯的例子則是:大學的二一制度。高等行政法院認為大學法施行細則逾越授權,但是報導顯示,教育部與立法委員都支持二一制度。倘若真被宣告因為逾越授權而違憲,那麼教育部還是會提出修正草案,立法院也會通過,那麼,在這麼無聊的輪迴之後,輸家是誰?是全民納稅人。事實上,大學法施行細則制訂好後,曾送到立法院過,想必立法院的教育委員會也看過,且他們也都接受這個制度,默示地同意了這個制度,而其他委員就算不是教育委員會的成員,也大都唸過大學,必定知道二一制度的存在,倘若他們真的覺得大學法施行細則違背了其本意,那麼他們早可以動手修改,哪用等到行政法院抓到機會來突顯自己的司法獨立﹗
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釋字第五二四號,涉及全民健保法的保費支付項目的行政命令,大法官認為其逾越了授權範圍。其實,這是立法機關有意的授權,因為立法機關知道自己真的不夠專業[71]。這個影響國家全體財政重要的法案,立法院希望授權給健保局多一點空間可以調度調配健保花費,結果大法官進來一鬧,改善了什麼嗎?﹗還有最近的證期會要求上市上櫃公司一定要設置獨立董監事的規定等等,涉及的都是極具專業與需要整體配套的行政問題,若大法官堅持運用授權明確性原則,我們根本無從強調政府再造,不但浪費許多立法、行政、司法成本,且許多法令都遲遲無法通過,對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也大打折扣。
本文從立法院事後監督機制的角度,批判了從德國引進的授權明確性原則,並且以簡單的經濟分析,說明為何事後監督的機制會比事前明確授權來得好。進而,對於為何我國憲法明明沒有規定,大法官卻硬是要引進這個原則,加以批判。但是,筆者深知,擁有決定何者為自然法的大法官們,是絕對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的,或許,要解決這個問題,不能祇是單純挑戰授權明確性這個原則而已,而必須要徹底挑戰司法違憲審查的制度設計--從法理學或從經濟分析的角度,才有可能扭轉乾坤。
*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所法律組碩士班
[1]因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所以原本授權命令與職權命令的區分,現已用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代替。本文為了統一及順應新法規定,故皆用法規命令以代替授權命令。
[2]許宗力,<行政命令授權明確性問題之研究>,《法與國家權力》,元照,219-225頁。
[3] 據張文貞八十四年間檢驗我國一千二百個法規命令中,只有一百零三個命令的授權有提供相當標準,佔8.6﹪,亦即若貫徹釋字第三一三號解釋,我國高達92﹪的法規命令與其授權條款都將會違憲。參考張文貞,《行政命令訂定程序的改革-多元最適原則程序的提出》,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1995,90-91頁。
[4]例如,葉俊榮、張文貞,<轉型法院與法治主義:論(最高)行政法院對違法行政命令審查的積極趨勢>,第一屆行政法實務與理論研討會,2001,21頁。
[5]許宗力,前註2,222-224頁。
[6]同上註,217頁。
[7]葉俊榮、張文貞,前註4,21頁。
[8]同上註,6頁。
[9]許宗力,<論國會對行政命令之監督>,《法與國家權力》,元照,269-300頁。
[10] 關於美國立法否決權的介紹,可參考湯德宗,〈三權憲法、四權政府與立法否決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INS v. Chadha案評釋〉,《美國研究》16卷2期,第27-99頁。有論者指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都已將立法否決權宣告違憲,筆者為何還特別強調立法機關的事後控制機制呢?於此必須說明,美國最高法院將立法否決權宣告違憲的理由,所採理由甚不合理,遭至美國學界諸多批評,且在立法否決權被宣告違憲後,國會仍然有採用立法否決權的形式來通過立法,無視最高法院的判決。雖然立法否決權被宣告違憲,國會仍在嘗試各種不同的事後監督機制,可見事後監督機制之重要。可參考,Frank B. Cross, Blake J. Nelson, Strategic Institutional Effects on Supreme Court Decisionmaking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95 Nw. U.L. Rev. at 1471. Richard J. Pierce, JR, Sidney A. Shapiro, Paul R. Verkuil,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1999), New York, New York Foundation Press, at 491-493.
[11]許宗力,前註9,273頁。
[12]湯德宗,<論行政立法之監督>,《行政程序法論》,元照,224-225頁,註85。
[13] Richard J. Pierce, JR, Sidney A. Shapiro, Paul R. Verkuil, supra note 10, at pp 61-62.
[14]許宗力,前註9,281-285頁。
[15]同上註,281頁。
[16]許宗力,前註2,225頁。
[17]Edgar Bodenheimer(美)E•博登海默,鄧正來、姬敬武譯,《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二十世紀文庫,華夏出版社,北京1987,144。
[18]相關的正反論辯,可參考,陳伯禮,《授權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北京,2000,17-31頁。
[19]林子儀,<美國總統的行政首長權與獨立行政管制委員會>,《權力分立與憲政發展》,月旦137-139。原則上,形式論與功能論的適用之處,乃在於對法條的解釋有所爭論,形式論是以法條字面的形式作解釋,而功能論則是以功能取向作解釋。授權明確性原則本來並非我國憲法明文的條文規定,所以可能不太適合拿來做比較,而筆者在此強調的,只是取功能論的精神。但是,在行政程序法制定後,授權明確性原則在我國算是有法條根據了,因而葉俊榮、張文貞即認為可以直接套用形式論與功能論的辯論,請參考氏著,前註4文。
[20]林子儀,同上註,138頁。
[21] George I. Lovell, That Sick Chicken Won’t Hunt: The Limits of a Judicially Enforced Non-Delegation Doctrine, 17 Const. Commentary 79, at 90-91.
[22] Jerry L. Mashaw,Greed, Chaos, & Governance: Using Public Choice to Improve Public Law, Yale University, at 139-140.
[23] Supra note 21, at 91-92.
[24] Eg., Ian McLeod, Legal Theory,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at 84-90.
[25]陳愛娥,<法治國原則的開放性及其意義核心-法制國內函的矛盾與其解決的嘗試>,《當代基礎法學理論-林文雄教授祝壽論文集》,2002。
[26] 國內對此譯語略有分歧,共有三種。一種是城仲模教授所譯「不得授權原則」,見城仲模,<論美國行政命令制度>,《行政法之基礎理論》,三民,1980,第103頁以下。一種是張文貞所譯「禁止授權原則」,見張文貞,前註3,第87頁以下。葉俊榮與張文貞又譯為「授權禁止原則」,見,葉俊榮、張文貞,前註4。
[27]關於美國禁止授權原則的發展,國內僅有城仲模於早年曾寫過一篇<論美國行政命令制度>加以介紹,近年則在張文貞的台大法研所碩士論文《行政命令訂定程序的改革-多元最適原則的提出》中有過簡短介紹。筆者認為,兩篇介紹並未抓住禁止授權原則發展的精神,且未突顯行政命令制定程序與授權明確性的功能互補問題。因而,筆者挑選美國兩本較為暢銷之行政法教科書,一本為Alfred C. Aman, Jr.與 William T. Mayton所合著的WEST教科書系列的《行政法》(Administrative law),另一本為Richard J. Pierce, Jr.、Sidney A. Shapiro、Paul R. Verkuil三人合著的《行政法和程序》(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比較兩本書中對禁止授權原則相關介紹的篇章,筆者認為後者篇幅較短但卻能清楚表明整個發展脈洛與相關學說討論,故選其做為寫作參考文本,也以其時間的分期、歸類為準。
[28] Richard J. Pierce, JR, Sidney A. Shapiro, Paul R. Verkuil, supra note 10, at pp 50-51.
[29] 11 U.S. (7 Cranch) 382 (1813).
[30] 192 U.S. 470 (1904).
[31] 關於可理解原則的內容,城仲謨的<論美國行政命令制度>一文中有清楚介紹,前註26。
[32] Richard J. Pierce, JR, Sidney A. Shapiro, Paul R. Verkuil, supra note 10, at pp 51-53.
[33] 293 U.S. 388 (1935).
[34] 295 U.S. 495 (1935).
[35] Bernard Schwartz, Administrative Law, in: Alan B. Morrison(ed), Fundamentals of American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4-135.
[36] Richard J. Pierce, JR, Sidney A. Shapiro, Paul R. Verkuil, supra note 10, at pp 53-56.
[37] Arizona v. California, 373 U.S. 546, 594 (1963).
[38] 337 F. Supp. 737 (D.D.C.1971).
[39] Richard J. Pierce, JR, Sidney A. Shapiro, Paul R. Verkuil, supra note 10, at pp 56-59.
[40] 448 U.S. 607 (1980).
[41] 542 U.S. 490 (1981).
[42] 488 U.S. 361 (1989).
[43] 論者指出,筆者如此強調允許廣泛授權,只靠立法機關事後監督機制作控管,但總不能連最嚴格的罪刑法定主義、租稅法定主義,也都一併廢棄。筆者認為,租稅法定主義但廢無妨,至於罪刑法定主義,則尚有探討餘地,不過不在本文討論之列。於此僅欲點出,美國對於罪刑法定主義,於本案似乎就呈現出不那麼堅持的態度。
[44] 葉俊榮,《行政法案例分析與研究分法》,三民書局,第296頁;張文貞,前註3,第91-94頁。
[45] 湯德宗,〈行政立法程序之研究:行政院經建會版「行政程序法」草案「命令訂定程序」設計構想〉,收於氏著《權力分立新論》,第397頁。
[46]單厚之,<立法院指因雜待太多實質修法的條文 提高複雜性才延但進度>,聯合報2001/09/01二版。
[47]林美玲,<數百法案待審 行政程序法最棘手>,聯合報2001/09/01二版。
[48] 公共選擇學是政治學上的重要理論,其理論的重心在於利益團體對政治活動的影響。美國公法學界於討論公法問題時,多半會運用大量的公共選擇學的理論,而我國學界則只見政治學者或經濟學者在討論利益團體對立法活動或個別管制議題上的影響,卻未見法律學者運用該理論來討論公法議題。國內法學界至今僅有數篇文獻介紹美國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例如,見黃銘傑,<利益團體與立法過程-以美國公共選擇理論之論點為中心>,《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8卷4期,677-698頁;但卻沒有將之用於具體的公法議題討論上。英文總論性質的文獻可參考Maxwell L. Stearns, Public Choice and Public Law: Reading and Commentary, Anderson Publishing Co. (1997). Jerry L. Mashaw, supra note 22.
[49] Peter H. Aranson, Ernest Gellhorn & Glen O. Robinson, A Theory of Legislative Delegation, 68 Cornell L. Rev. 1 (1982),in: Maxwell L. Stearns, supra note 48, at 158-159, 171-172.
[50] Richard J. Pierce, JR, Sidney A. Shapiro, Paul R. Verkuil, supra note 10, at 44.
[51] 詳細的論述,可參考黃銘傑,前註48文。
[52]Peter H. Aranson, Ernest Gellhorn & Glen O. Robinson, supra note 49, at 160, 171.
[53] Jerry L. Mashaw,supra note 22, at 142-5.
[54] Peter H. Aranson, Ernest Gellhorn & Glen O. Robinson, supra note 49, at 164-168.
[55] Isaac Ehrlich, Richard Posner,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Legal Rulemaking,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Ⅲ(1), Junuary 1974.
[56]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s Analysis of Law (4th)1992, at 542.
[57] 關於立法產能的限制,政治學者比較有關心並加以討論,例如,可參考楊泰順,《被誤解的國會》,第四章:議員人數與問政風格,希代出版,第88頁以下。
[58] Isaac Ehrlich, Richard Posner, supra note 55, at 269-270.
[59] Charles L. Gay, James Essinger,盧娜譯,《企業外包模式》,商周,2001。
[60] 同上註,178-193頁。
[61] 對我國憲法釋義學發展的剖析與觀察,可參考蘇永欽,〈部門憲法--憲法釋義學的新路徑?〉一文第貳部分、釋義學蓬勃發展下的困境,收於《當代公法新論(上)》,元照,2002年7月,741-747頁。
[62] 有人或許會抗辯大法官並無解釋文中明確講出「比例原則」四個字。這樣的抗辯非常薄落弱,事實上,大法官於解釋理由書、不同意見書,或其本身發表的論文中,一再地使用「比例原則」四個字。
[63] 葉俊榮將這種認為外國法制比較優越的心態,稱為「法律殖民主義」,請參見氏著,《行政法案例分析與研究方法》,第4-5頁。對於這個現象,也有學者用女性主義來加以分析批判,請參考陳昭如,〈創造性別平等,抑或與父權共謀﹖--關於臺灣法律近代西方法化的女性主義考察〉,《思與言》第40卷第1期,第220-231頁。
[64]蘇永欽,<結果取向的憲法解釋>,《合憲性控制的理論與實際》,月旦,266-269頁。
[65] 從法治斌教授於1995年對各大學法律系教授作的一項抽樣調查顯示,目前留美的學者,已經漸漸多過留德的學者,這某程度也蠻符合大法官解釋漸漸從德國風轉向美國風的趨勢。請參見法治斌,〈法律學門之項況與展望〉,《科學發展月刊》第25卷第5期,第286-288頁。
[66]蘇永欽,<大法官解釋與台灣的社會變遷>,《合憲性控制的理論與實際》,月旦,304-306頁
[67]廖國宏,<論行政處分踐行正當程序之憲法基礎-「正當程序平等保障說」芻議>,李模務實法學基金會第六屆法學論文徵選優勝作品集,2002,5頁。
[68]David P. Curri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8),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t 46.
[69]廖國宏,前註67,19-20頁。
[70] Jeremy Waldron, Law and Disagreement (199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308-309.
[71] 關於該案的評釋,可參考蔡維英,<專業行政領域之授權立法>,《月旦法學雜誌》第74期,179-184頁。